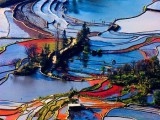关于土地流转问题,今年的两会上,也是一个热点。据2009年3月13日《中国国土资源报土资源报》报道,农村抛荒土地该如何有效处理?土地流转中是否会出现“大地主”?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中扮演什么角色?关注“三农”,推动农村土地流转,是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笔者认为,土地流转,关键在于要让农民得实惠。十七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加明确提出了“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这一目标。2003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条也明确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
自八十年代农民享有稍微稳定一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后,农民就已经开始自发地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在同时也始终伴随着另一种形式的土地流转,即基层政府、或者村集体拿本来属于农民的土地进行流转,包括实行规模经营。近几年来,这种流转的形式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包括各地出台的撤村并镇计划、以宅基地换房计划等。表面看起来,这样的做法能够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使土地用以更有价值的用途,增加土地的产出。问题是,土地如此流转的主体是地方政府或村集体,它们推出各种各样的土地流转形态,要求农民参与,有的时候甚至是强制农民参与。不难理解,由此所实现的效率与农民无关,农民没有充分享有效率改进所带来的收益。相反,很大部分收益被那些积极地推动土地流转的地方政府、村集体占有了。
从本质上来说,土地流转是农民实现自己经济利益的一种形式。这种利益是农民依据土地承包法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我国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制,家庭承包经营制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集体土地经营制度。它是在承认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将土地的经营权和收益权以承包的方式赋予农民;农民家庭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在国家计划与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有权按照自己的特长和优势独立自主安排生产经营活动;生产收益除完成年初确定上交给国家和集体的任务外,都归自己所有。也就是说,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作为农民的利益而存在的,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农民可以通过经营土地实现这种利益,也可以通过流转来实现这种利益。
但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制约,农民的这种利益并不是作为财产权而存在的,国家不允许农民把土地经营承包权用作抵押,国家的有关法律对农民实施这些权益作出了许多限制。比如《土地承包法》第26条就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这些规定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利益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也限制了农民进城的步伐。正因为如此,十七届三中全会才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承包经营权,在保持现有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并通过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引导农民以转包、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进一步明确农民土地流转是农民的法定权利,是对土地作为农民财产权的一种宣示和保护。
如果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所谓权利是法律对公民或法人能够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并要求他人相应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就土地流转作为农民的权利而言,它要求农民可以流转自己承包的土地经营权也可以不流转,任何妨碍农民土地流转的行为都是对农民法定权利的侵犯。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农村土地流转时一定要坚持依法、自愿和有偿的原则。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应该说,这些原则基本上体现了土地流转各方的利益,这是必须坚持的。这其中坚持农民自愿有偿的原则特别重要。农民自愿进行流转是合法的基本条件。在目前的情况下,要特别警惕强制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行为。国家应从权利保护的高度,有明确的权利救济手段,确保流转符合农民的意愿,要坚决制止有些地方官员为了所谓的政绩或为了与不良商人勾结获利而假借土地流转之名,骗取农民的土地。面对日益强大的掠夺,农民有对那些侵害自己利益的土地流转说“不”的权利,而保护农民的这些权利则是国家的责任。
必须借助特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使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制度创新能够真正具有改进农民福利的效果。这一制度安排其实不难,就是让农民享有更为稳定、充分的土地权利,让农民自己来决定怎样利用土地,让农民自发地创新各种流转土地的新制度。目前,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没有采取这样的态度。相反,却热衷于自己提出各种各样的土地流转方案。其中某些方案把农民从土地的主人变成了无足轻重的角色,事实上是扩大地方政府进行土地经营的范围,从城市国有土地扩大到乡村集体土地上,借以获得土地财政收益。中央政府果断叫停这样的做法,是有必要的。农民当然希望对土地拥有更充分、更稳定的权利,从而获得稳定收益。而一些地方政府却希望实现农业产值的快速增长,希望通过圈占土地,获取更多经营土地的财政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密切监督各地政府出台的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很有必要。更重要的是,借助细密的制度设计,更为充分、有效地保障农民对土地的权利,使农民可以抗衡一些地方政府、村集体不合理的流转安排。农民有了这种权利,自然会自发地创造出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只要农民有权利,土地自然会合理地流转。否则,地方政府、村集体、城市资本趁虚而入,由此推动的土地流转必然会导致严重经济与社会问题。 {Npage}
当前在一些地方,农民承包土地流转权被剥夺了,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往往越俎代庖,成为流转主体;市场流转被弃之不用,主要通过行政手段流转;流转收益仅给承包农户部分“补偿”,相当的收益被乡镇政府和村集体所占有了。这些做法严重侵害了农民利益,偏离党的土地承包政策,引发了大量土地纠纷,成为当前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些情况应当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土地流转中的错误做法必须及时纠正,违纪违法行为必须严肃查处。为什么一些地方的干部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喜欢自作主张,而置党的农村政策于不顾呢?在一些人的眼里,农村土地流转是一件有厚利可图、有油水可揩的好事。利字当前,什么维护农民利益,全都不管不顾了。一些地方在农村土地流转上的强迫命令及“反租倒包”“预留机动田”等花样,其实就是与民争利。
另一种情况是,一些干部在农村经济发展思路上出现了偏差。眼下在一些农村干部中存在这样的“高论”:如让农户自愿流转会“阻碍”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土地流转离不开行政干预”等等。这些错误认识的存在,使一些地方土地流转工作的方式从“引导”变成了“逼迫”,干部作风简单粗暴,在农村造成了新的矛盾。认识上的这种偏差,根源在于有的干部对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认为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对农业生产力的推动力“已经释放完毕”。这种认识不符合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实际。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家庭经营的效率最高,它不仅适用于传统农业,而且适用于现代农业。我国各地近年农业产业化的成功实践,都是在农户经营基础上实现的。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合作经营和产业化经营,才是实现农业高效益的必由之路。
大多数农村家庭仍以家庭经营为主要收入,劳动力转移对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促进作用尚未有效发挥;农业龙头企业发展还不够,带动能力还不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推动了土地流转方式的创新,但由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以及内部制度建设滞后、农民的参与意识不强等问题的存在,没有更好地发挥作用;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确权、农民依法维权的意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土地流转信息中介服务滞后,影响了土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让土地流转真正成为开拓现代农业新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助推器”,就要正确理解土地流转与产业发展的关系,防止“为流转而流转,为集中而集中”行为,坚决杜绝在土地流转中出现政府不当干预和强迫流转的现象。现代农业可持续的发展是土地流转的动力和目标,要以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创造土地流转需求,并以合法有序的土地流转为产业的融合与发展创造必要的条件。
进一步培育土地流转市场,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力度,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改善收入结构,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的需求。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和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充分发挥他们的辐射作用和组织作用,形成与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和产业化相适应的土地流转市场。建立土地流转信息中心,增强政府的信息服务功能。在土地流转中,政府应回归到服务者的本位,才能作到“到位而不越位”。应加快推动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工作,进一步加大法律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引导他们规范地进行土地流转,并维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对于土地流转中违法改变用途等问题,应当通过加大执法力度等方式,及时进行查处,从而引导土地流转市场朝合法有序的方向不断发展。
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现行的土地使用权以及流转的法律政策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的需求。例如,农用地用途限制、农民宅基地的使用与流转限制与生态农业、观光旅游农业等新型综合农业开发、服务业态的发展不相适应。新型的农业业态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呼吁农用地、宅基地的制度创新。因此,应当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在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前提下,努力规范土地入股的流转方式,并探索土地流转的新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在引导和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中,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有农户对农户、农户对协会、农户对企业等。其中,农户对农户流转的土地基本上还是用来耕作粮食作物,而其他形式流转的土地多数没有种植粮食作物,而是选择了种植蔬菜、烟草、花卉、树苗,或者直接用来挖塘养鱼、修圈养畜。虽然土地用途仍然属于农业范畴,但用于种植各种经济作物显然成为首选。
还有一些地方,把本来种粮的土地用来搞成观光农业、休闲农业,虽然可能还是种植粮食,但种植追求已经发生改变,多产粮食已不再是根本目的,这对国家粮食安全构成了一定威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是当前促进农业稳定发展的重要内容,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要千方百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绝不是鼓励“非粮化”种植。主要原因是种粮收益远远低于种植其他经济作物和搞养殖的效益;还有一个原因是农村干部和群众有一种误解,片面认为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都是农业生产用地。
必须处理好高效农业与粮食种植的关系,处理好种粮效益与其他经济作物或养殖效益之间"剪刀差"的问题。应尽快建立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制度,加大对种粮农户、协会、企业的补贴力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和粮食保护价水平,确保粮食主产区得到合理利益补偿,确保种粮农民和业主得到合理经济收益。还必须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基本农田保护的政策宣传。要旗帜鲜明地宣传流转的基本农田不准用来进行植树造林、发展林果业和搞林粮间作;不准以农业结构调整为名,在流转的基本农田内挖塘养鱼、建设用于畜禽养殖的建筑物等活动。
总的说来,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证明,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制度。在新时期新阶段,它当然要不断完善。但千变万变,户为基础的土地联产承包制度不能变。有了这个制度,农民就有了“定心丸”,就有了生产自主权,就有了生产积极性。有条件的地方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必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以尊重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为前提。土地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根,是农民作为经济主体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最基本的资源和资本。稳定农户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是亿万农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农村政策的基石。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不能有丝毫含糊,更不允许以种种借口侵犯包括承包土地流转权在内的农民合法权利。